引言
主日晚崇拜之后,我在荣耀中出生。我的父母是五旬宗的先驱,当时他们住在主日学校几间教室里,这间教会是他们自己创立的,位于弗吉利亚州首府里士满(Richmond,Virginia)。他们的事工充满神的荣耀,我就这样出生了。
少女时期,每周三下午我直接从学校赶到教会。从一点到四点,教会的虔诚基督徒都会聚集在一起祷告,我参加了大部分的祷告聚会。
前两小时,他们在神面前祷告和代祷,而最后一小时总是沉浸在神的同在中,这真是最美好的时光,他们会为每一件能想到的事情代求,然后圣灵就会接管。在那些年里,荣耀的声音进入我灵,保守我在世界各地的事工。
我参加无数聚会,听过无数布道,但影响最深的就是这荣耀的声音——来自祷告会的最后一小时,在这里,属神子民触摸到了永恒的领域。
就像空气是地上的大气层,荣耀是天上的大气层。它将我们高高举起,远离地上,与神同在。
后来,我定居耶路撒冷,在锡安山敬拜神之后,主指示我从赞美到敬拜直至荣耀的进程,以及这三样之间的关系。我将这些简单的真理分享给全世界的基督徒。赞美再赞美……直到敬拜的灵降临,敬拜再敬拜……直到荣耀降临,然后……站立在荣耀中。
如果你能掌握赞美、敬拜和荣耀的基本原则——它们是如此简单,以致于我们会常常错过——你就能在神里面拥有其他任何想要的。独自一人,或无人与你同心祷告,这并不重要。你处于灵性成长的何种阶段,这也不重要。
进入荣耀的领域,一切皆有可能!
地,和其中所充满的;世界,和住在其间的,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,安定在大水之上。
谁能登耶和华的山?谁能站在他的圣所?就是手洁心清,不向虚妄,起誓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,又蒙救他的 神使他成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,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〔细拉〕
众城门哪!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永久的门户,你们要被举起!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?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,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哪!你们要抬起头来!永久的门户,你们要把头抬起!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?万军之耶和华,他是荣耀的王。〔细拉〕
诗篇24:1-10
赞美再赞美…直到
敬拜
的灵
降临。
敬拜再敬拜……直到
荣耀将临
之后…
站立在荣耀中!
第一部分:赞美
赞美再赞美……直到敬拜的灵降临。
第一章 赞美:收割的工具
赞美诗:等候赞美你
主啊,在锡安等候赞美你,
主啊,在锡安等候赞美你 ,
主啊,在锡安等候赞美你
等候赞美你 ……
耶和华说,那日我必应允,我必应允天,天必应允地;地必应允五谷,新酒,和油,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(耶斯列就是神撒种的意思)。
我必将他种在这地,素不蒙怜悯的,我必怜悯,本非我民的,我必对他说,你是我的民,他必说,你是我的神。——(何西阿书2:21-23)
赞美是大收割强有力的工具!
如果有什么是我们五旬宗基督徒认为自己知道该如何做的,那就是赞美主。我们或许会知道自己其它的不足,但说到赞美,从某种程度上说,我们已达到博士水平。
1972年秋,神带领我们定居耶路撒冷,并就有关犹太人的事工对我们说话:“虽然你们对此一无所知,但不要有丝毫忧虑,我将以我的灵指教你。”
我并不介意主的责备,当人们责备时,我们会感觉非常糟糕。但当主责备我们时,祂会赐给我们欠缺的答案。在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之后,他说:“我将给你们指明方向。”
我们曾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了几星期。在这期间,我们和来自维吉尼亚州亚什兰(Ashland, Virginia)营地的二十五名年轻人一起,一周四个晚上在锡安山上的鸡鸣堂(St. Peter en Gallicantu,坐落于基督时期大祭司该亚法家旧址上,是一座的美丽的天主堂)赞美敬拜主,白天则参加每天五小时的希伯来语课程。
一天晚上,一位曾在尼日利亚工作的美国牧师拜访我们说,看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,就知道他们应该出去分发福音小册子。以他过去的经验,他可以想像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触及整个耶路撒冷,并能计算出分发多少万份的福音小册子,“你们必须出去撒种。”他说。
这位弟兄说的每件事都是圣经真理。我们相信在其他国家播种神的话语,完成伟大的圣经和福音书分发计划。在尼泊尔,我们甚至带着福音书租用直升机到偏远山区,在皇室家族成员的帮助下,穿越障碍分发它们。但在耶路撒冷,有一定限制,我们若要住在那里,必须遵守当地法律。
虽然这位弟兄说的都出自圣经,但不是当时神对耶路撒冷的答案,神对每个国家都有祂的计划。各地都采用同一答案,或用同一个方案来解决所有情况,这是毫无必要的。
那位弟兄正说话的时候,我可以感受到年轻人正受到挑战。甚至可以想象到,第二天一早,这二十五名年轻人就排队问:“福音小册子在哪里?我们准备去分发它们。”
那天晚上,我祷告说:“主啊,赐给我你的答案。”
那天半夜,主对我说:“你若向天上撒种,我将在地上撒种。”这就是我们锡安山赞美事工的由来。
我手边没有准确的圣经经文支持神对我说的话。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祂的意思,“你若向天上撒种,我将在地上撒种。”但我下决心学习。
夜复一夜,我们聚集在一起赞美主,主对我们说:“你仅仅刚刚开始赞美我,我将教你如何以我的灵赞美我。”我仍不断学习。
我们称颂神一段时间后,就会获得先知性话语,主说:“赞美讨我喜悦;激动我心;令我高兴。但我想要你更多地赞美我。”我们很快学到主是如此喜悦赞美,祂总是想要更多。
总有一些这样的教导四处飘荡:“赞美是为了不成熟的基督徒预备的,而代祷才是属于成熟基督徒的。”但这与真理相差甚远,在《启示录》里,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赞美书卷之一(事实上是记载天上赞美敬拜的书),我们可以读到:
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,神的众仆人哪!凡敬畏他的,无论大小,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
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,众水的声音,大雷的声音,说,哈利路亚!因为主我们的神,全能者,作王了。
启示录(19:5-6)
谁是这些“仆人”?在神的日程中,那些到《启示录》十九章才出现,蒙召来赞美神的,就是祂“所有”仆人。若赞美是不成熟的,进入永恒之前一定不再赞美。
这段经文进一步描述这些蒙召来赞美神的人,称为“凡敬畏他的”,最后称为“无论大小”,都要赞美主。在赞美的领域,我们都是平等的。无论“大”、“小”都要赞美神,在赞美的领域我们合而为一。
约翰回应神的呼召,形容所听到的为“群众的声音”。神所赐最伟大的赞美乐器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,要学会向神扬声。我们发现神不仅喜悦我们颂赞祂,还想要更多,祂也喜欢我们更大声地赞美祂。
不仅激励我们“赞美主”,而且告诉我们用“称谢的声音”(诗篇26:7)、“夸胜的声音”(诗篇47:1)、“诗歌的声音”(诗篇98:5)和“欢呼的声音”(诗篇:118:15)颂赞祂。
使徒约翰听到“群众的声音”、“众水的声音”、“大雷的声音”。我们的赞美直冲云霄,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或利文斯顿大瀑布(Niagara or Livingston Falls)的水声,如此巨大的响声汇聚在一起,越来越大直到到“好像……大雷的声音”。
约翰听到有声音说:“哈利路亚!因为主我们的神,全能者,作王了。”赞美的声音永远是得胜的声音,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总是与赞美争战。长时间赞美主而未得胜,这是不可能的。有时你为一些事情祷告,你越多地宣告问题,并为此祷告,却发现信心就越动摇。你起初看待这些问题就如实际一样,但这样做以后反而把它们看得更大了,最后就是束手无策。但当你转向赞美,总是进入得胜。赞美就是进入,“当称谢进入祂的门,当赞美进入祂的院……”(诗篇100:4)
赞美不是终点,而是开始,是进入。许多五旬节宗和灵恩派基督徒已学会籍着赞美进入,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持续赞美进入敬拜,直到神的荣耀来临。赞美就是进入神的同在,经由赞美之门进入神的同在。
新年前夕,有六周左右,我们持续在锡安山赞美主。不断被主激励,越来越深地赞美神。以嘴唇赞美他,鼓掌赞美他,举起双手赞美他,跳舞赞美他,以圣经记载的各样美好方式赞美他。
新年前夕,主对我们说:“就在此时,当你们赞美我时,我的灵浇灌在耶路撒冷另一区。”我们异常兴奋,几乎都等不及第二天来观看神在那里所做的了。
第二天,我们得知二十五名阿拉伯裔浸信会的年轻人晚上聚集在一起,突然圣灵来浇灌他们,他们开始说方言。你要知道,在当时,耶路撒冷的二十五人可是相当于美国的二千五百人。
我们激动不已!我们正在学习学习认识神的方式,正如先知弥迦所说的:
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,说,来吧,我们登耶和华的山,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;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;耶和华的言语,必出于耶路撒冷。
弥迦书4:2
神曾应许教导我们,祂也是这么做的。教会曾太长时间试图用麦迪逊大道方法(Madison Avenue methods,是一种世人营销的方法,这里指用世人的方法传福音),即人为的方法、自己的聪明为神工作。但是,当我们以神的方法做事,就获得神的果效。
曾经我们要学太多的东西,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胆无拘束。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,一旦你发现发生了什么,就想再试一次。我们以更大的期待投入事奉,以更大的热诚赞美主。几周后的一个晚上,主说:“当你们赞美我,我的灵在加沙浇灌。”我们就开始听说圣灵在加沙浇灌的消息。
几周过去了,神又对我们说圣灵在加利利浇灌,随后,我们就听到这消息。更多时间过去了,主对我们说,“我必到犹太人,我的民那里,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亲自显现给他们看——就是基布提(犹太公社)、田野、工厂。”于是犹太人向我们敬拜之地涌来,告诉我们,他们得到耶稣的个人启示。
我们学会在耶路撒冷赞美主,向天撒种,神收取我们的赞美并在地上撒种,——耶路撒冷、加沙、加利利——直至以色列全地。后来神开阔我们的眼界,看见赞美同样在地极进行大收割,赞美是神国最有力的收割工具之一。
几年前,随处可以见到汽车保险杠上贴着标语:“无论怎样,都要赞美耶和华!”意思是:“不论喜欢不喜欢,总要赞美神。即使从工作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,或者过了郁闷的一天,无论怎样,总要打起精神,开始赞美神。”只要听到有人这么说,我的灵就被搅扰。
我问神,为什么这个说法会令我心烦。祂指示我,旧约中献上给神的祭物必须是完美的,没有瑕疵的,而我们被教导,神能接受任何陈旧的赞美。
我说:“但是主,这是真的,有时来神的殿感觉并不太好,我们并不总是喜欢赞美神,因此,这个教导有真理的成分。主啊,请赐给我这个问题的答案。”
我们都学到过有关颂赞为祭的经文:
我们应当籍着耶稣,常常以颂赞为祭,献给神,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——希伯来书13:15
这里确实说到“以颂赞为祭(物)”,但许多人引用这节经文时,对于“祭物”的理解好像这个词从未在旧约出现过一样。犹太人的确有许多缺点,但是他们从未抱怨给神献祭。对我们而言,“献祭”是如此艰难,似乎必须付出代价。这样人们说:“让我们献上颂赞为祭”——意味着:“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。”
一天,我正读到《以赛亚书》这一段:
我造就嘴唇的果子…… 以赛亚书57:19
我顿时明白,若要献“祭”且祭物是“(我们)嘴唇的果子”,若是神创造的,我们无需费力。我们来到主的殿说:“主啊,在我里面创造出赞美。”于是,忽然觉得内心最深处开始一点点冒出“哈利路亚”、“阿门”、“赞美耶和华”或其他赞美的话,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赞美主。
一次,我见一位女士手中拿着一张小纸条站在主面前,敬拜时偶尔看看。“那是什么?”我问她。
“这是我赞美的词汇。”她答道,我对此并不介意,因为我知道她是真诚的,她想献上最美的颂赞。但不用担心“赞美的词汇”,来自内心最深处创造性的赞美,哪怕只是一个“阿门”,也远远超过只是嘴唇上的宏伟词汇。有一度,我发现自己在反复说:“阿门!阿门!阿门!阿门!”这是圣灵在教导我,祂就是我生命中的阿们,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字,祂就是“我心所愿”(the So Be It),是让阿门过的事情实现的那一位,是让阿门过的事情成型的那一位。这不是从书中读到的,而是圣灵使之成型在我里面。
如果你只会说“哈利路亚”,而这个“哈利路亚”是创造出来的“哈利路亚”,这就足够了。我总是告诉人们,我刚才说的“哈利路亚”不是我还是小女孩学会过的“哈利路亚”,也不是上周在耶路撒冷献给神的“哈利路亚”。这“哈利路亚”是全新的,就像开口说方言是超自然的,它也是创造性的。
每一个“哈利路亚”都有深意。当你对你的另一半说:“我爱你”,那三个字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,但也有更完整详尽的启示。你在一个背景说它,下次换了另一个背景,因此“我爱你”不是静态的,它在不断变化,其中有生命——这是生命的话语所带来的。
这就是我在赞美时发生的事,“哈利路亚”不是静态的,它伴随着生命的流淌,带着赞美走向永活的主。
在九岁时我就在说方言,不明白说的是什么,一句话都不明白。有时,在方言中神赐我人名或地名。我只记得这些,除此之外,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说方言不是透过思想,它发自灵,我所说的创造性的赞美也是一样。
我不是在想:“我要赞美主。”就在神的灵透过我运行的时候,我进入祂的同在,我灵向祂敞开,我的嘴开始自动宣告赞美,我就发现自己在赞美神了。籍着这赞美事奉,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祂。
这就是神关于献上“颂赞为祭“的意思,它不是痛苦的献祭。这献祭蒙主悦纳,我也同时得喜悦。我发现自己在主临到时,不再是结结巴巴的,而是满溢、沸腾、不能自已的。
“你是如此美妙,耶稣。你是多么美丽,你是多么喜乐,你很可爱,我的爱,你是如此可爱。”说这话很容易。
我们需要阅读《诗篇》,让它的语言成为我们的灵魂,成为我们的性格;我们阅读《雅歌》,让神激动我们的言语,如圣经所说,成为“快手笔”(诗篇45:1),成为一支描写和宣告主赞美的笔。神希望祂的灵在我们里面流淌,好让我们不会只是静默无语地站在那里。
多少次我们想听到祂的声音啊,但在《雅歌》里,新郎对新娘说:“我想看见你的面,听到你的声音。”神赐给我们声音扬声赞美祂,若我们有什么可献给祂,那就是美好的声音。
有一次,我曾遇到车祸,下巴上的小窝提醒我当时所发生的一切。我的下巴受伤太重,以至于好几天都无法出声。我曾听人们说:“我可以在里面不出声地赞美神,这是一样的。“但我发现这大不相同,以前无法反驳他们,无法说是相同还是不同的。但经历过不能大声赞美神以后,我知道那是不一样的。
以可以听得到的言语赞美神是一种释放。当你张开嘴巴,开始在活人之地宣告主的良善,宣告主所行的神迹,宣告主的医治,宣告主的得胜,宣告主的更新的时候,当你使用你的声音成为号角,流出主的祝福,就会释放神的江河,而且是源源不断地从你里面流出。
你越多宣告祂的祝福,就越多要宣告的;你越多谈论祂的良善,就越多要述说的。
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,直到永远。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。(诗篇89:1)
我要传扬,要用声音,要为神的国、为神的荣耀使用它,赞美神!
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。他们仍要(英文版可以翻译为“持续不断地”)赞美你。〔细拉〕(诗篇84:4)
我们从不厌倦赞美神,我们将“持续不断地要赞美他”。我希望人们发现我在“持续不断地要赞美”主,我想跻身赞美者之列,而不在批评者或是抱怨者之列。
有一次,我们去了埃及,苏珊姊妹带回了奇妙的启示。她说:“路得,我突然就知道了抱怨的灵是埃及的灵。”直到今日,这灵仍一直存在。神不希望我们以任何方式有埃及的灵,祂希望我们成为赞美祂的天军。天军赞美主,我们更有理由赞美神,因为我们籍着羔羊的宝血得了救赎。天军在神的同在中,日日夜夜不住地赞美神。
许多人发觉,以他们年幼的灵性,要抓住圣经经文不断祷告是很困难的。在我们的许多活动中间,许多次都是在有意识地赞美敬拜,然而一旦你进入到赞美敬拜中,即使在工作中,都会下意识涌流出赞美上达神面前。即使你在睡眠中,你也会下意识地赞美敬拜。有人可能会听到你在夜里翻身,说起别国的话来,并不意味着你很属灵,而是因为这实在无需努力,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就像自然呼吸一样,在神里有一领域称为“持续不断地赞美神”。你认识到圣灵的信实,祂即你里面的圣灵就会接管,就会赞美——甚至就在你一直焦虑的时刻。在某一层面上,你关注接下来的状况。你突然发现,在这个层面上,你正在思考,正在焦虑,寻求答案,而在另一层面,圣灵已经透过你在唱歌。你一直在歌唱,甚至自己都不知晓。
当你突然听到自己在歌唱,就会意识到是圣灵正在赞美,圣灵是满有信心的,祂并不担忧,你里面的圣灵满有平安。在神里面赞美的维度完全控制了局面,你只需离开自然层面,让圣灵占据优势就行了。
耶路撒冷啊,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,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呼吁耶和华的,你们不要歇息。(以赛亚书62:6)
我喜欢这节经文。你看见了其中的对比了吗?一方面非常紧张:“不要歇息”,坚持,一直都在做。另一面则是轻松自如:“呼吁耶和华的”。
我们听到有人说“我们要轰炸天上。”神说:“呼吁耶和华的,你们不要歇息”。如此轻柔:那是主的歌,主的赞美,而不是努力祷告。
我们的祷告太沉重,以致于我们需要属灵的“查尔斯.阿特拉斯”(Charles Atlases,专教健身长肌肉)们或是“超人”,其实不需要这样。只要呼吁主,说:“耶稣,你太奇妙了!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!”只要一直歌唱、一直赞美。
这样,夜间醒来,你就能歌唱而不是痛苦不安。
也不要使他歇息,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,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(以赛亚书62:7)
神已拣选耶路撒冷,祂对圣城的愿望没什么要大过让她成为可赞美的,在全地成为可赞美的,这也是神对你我的期望。有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志向,但若简单地进入成为赞美神的云柱,赞美神的楼,在地上赞美神,在人群中赞美神,神就将提升我们
我们开始在耶路撒冷向天撒种之后,有人指出何西阿书2章21-23节的真理:
耶和华说,那日我必应允,我必应允天,天必应允地,地必应允五谷,新酒,和油,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,〔耶斯列就是神撒种的意思〕
我必将他种在这地,素不蒙怜悯的,我必怜悯,本非我民的,我必对他说,你是我的民,他必说,你是我的神。
“耶斯列”就是“神撒种”之意。主坐在天上,听到我们向天撒种。祂说:“我必应允天,天必应允地”。因为我们已然向天撒种,作为回应神就在地上撒种。祂不仅是收割者,也是撒种者。我们从不怀疑神是收割者。他是全地的首席收割者,我们深知这点,但我们不知道祂也是首席撒种者。我们认为做了所有撒种之工,不!祂才是首席撒种者。当我站着赞美神,我是向天撒种。作为回报,地上收到“五谷、新酒和油”——这是复兴的象征。
有些人很难相信,他们只是能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赞美神,以这种方式帮助带来社区复兴。通过播下赞美的种子,你不仅可以影响所在的社区。当你能站在某地赞美事奉主,它甚至可以深远地影响复兴,直到地极。向天撒种吧!
如果我们不小心,我们作为属灵的年轻人学到的事情,以后要学得“更好”,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为了看似“更深”的真理,而撇下之前所学的。然后,神不得不激发、提醒我们,祂想要的仍是那教给我们的至简的真理。
几年前,我在去澳大利亚的路上。我以折扣价买了从伦敦起飞经由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机票。多年来,国泰航空公司一直飞悉尼和墨尔本的航线。然而,在去伦敦的路上,我在座椅口袋里看到了国泰航空公司航班时刻表,惊奇地发现,他们现在从香港飞往珀斯(Perth)的航班,如果直飞珀斯,我将节省个四、五百美元。但是他们愿意改签机票吗?通常航空公司不大乐意改签以折扣价购买的机票。
爱丽丝.福特姊妹在香港机场接我。“你可以在香港呆多长时间?”她问。
“好吧,如果我飞往悉尼,就只有四、五个小时。但若飞往珀斯,就可以过夜。稍等一下,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。”
当我询问办事人员的时候,她说:“是的,我们很乐意改签,这样你就能飞往珀斯。”
在珀斯没有人知道我的到来,但我一到那里,唐.罗杰斯牧师(Rev. Don Rogers)就非常高兴地问我:“你能安排三个晚上教导我们赞美、敬拜和荣耀吗?”我很乐意这样做。
我在那里的教导和现在正做的一样,先讲述在耶路撒冷的经历,一两天之后牧师对我说:“路得姊妹,我们学到了:三年前教会刚成立时做事的方式是正确的,我们这样做,是因为圣灵带领。然而,最近两年里我们学到了‘更好’的方式。神差你来是让我们知道,起初的简单方式正是圣灵的方式。我们需要回到圣灵的水流,像神起初所教导的。”
如果丢弃赞美,在神里你永远不会取得太多进步。永远不会!当你听到有人说:“赞美是肤浅的。”就知道他们需要赞美的深入启示。
主带领我们到更广阔的领域、更多的容量、更大的能力、更高超的技艺。祂教我们如何收获更多会友,如何在赞美中踏出信心的步伐,如何在赞美的领域让信心运行(如同我们为病人祷告或服事别人的需要时,我们让信心运行,我们正踏入在神里赞美的新区域),而且我们将在无尽的永恒中持续赞美神。我们永不放弃赞美,赞美是永恒的,正如神与我们都是永恒的一样。
我们用“悟性”赞美神——英语、法语或西班牙语。在维吉尼亚州的露天营会上,有时我们有将近三十种语言来赞美神。在耶路撒冷,大约一百个国家的基督徒每年都来与我们一起赞美、敬拜。当我们用各自的语言一起赞美神时,那是何等美妙啊,然后,我们会用以圣灵带给我们的美丽言语来赞美神。
但以理预见到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事奉神(但以理书7:14),他们述说赞美、敬拜和崇拜的话来事奉祂。
有些人对用舞蹈来赞美神有疑问,我很理解,因为我曾是其中之一,虽相信跳舞是符合圣经,但非常乐意其他人为我这样做,我自己则不愿意。当时,我们教会只有少数人跳舞——我的母亲和其他两三个人。跳舞不像现在普及,被人接纳。喜乐之灵萦绕在我们中间,我总无法融入其中。
教会事工中学到的坏事之一是如何在“圣工”中保持忙碌,一种“神圣的忙碌”。我那时正弹钢琴或风琴,总是无法跳舞。之后,有一天,主对我谈论大卫返回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他和神的约柜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时,沿途一路跳舞。
有人告诉大卫王说,耶和华因为约柜,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,和一切属他的。大卫就去,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,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
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,大卫就献牛,与肥羊为祭。
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,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
这样,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,欢呼吹角,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,扫罗的女儿米甲,从窗户里观看,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,心里就轻视他。
撒母耳记下6:12-16
主指示我,如果我也想带着神的约柜,我们也要跳舞。
大卫成功地将约柜带回来之后,分给所有帮忙的人一块肉、一个饼,和一个葡萄饼(撒母耳记下6:19),他因此成为圣经中唯一供养整个国家的人。
耶稣曾一次喂饱四千人,另一次有五千人,这是圣经中其他有关喂饱他人的神迹。然而,除了大卫以外,没有人可供养一整个国家,但大卫一路跳舞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做到了。除了大卫,没有人可以以三倍的分量喂饱别人。
主对我说:“如果你想供养一个国家,如果想以三倍的分量供养,就必须跳舞。”祂没有告诉我为了得救或进入天堂而跳舞,或跳舞成为当地教会活动的一部分。祂只是让我知道舞蹈会带来全国性恩膏,以及圣灵源源不断浇灌。如果想以三倍的分量供养一个国家,我不得不跳舞。
我一直在周游列国,曾四年在香港事奉主,在日本、台湾和印度讲道。在印度我向很多人传道,已蒙祝福。无论到哪里,我都曾见证复兴。现在,神向我谈论关于进深地事奉,在神面前扩张地界。
我喜爱主的挑战!我们必须籍圣灵的挑战而活。别人提出好建议时,人性的一面使我们反抗,但主向我们说话,最好侧耳倾听,我们需要学会像回应神一样回应主的仆人。许多时候,神借着神仆来对我们发出声音。
(跳舞这件事)对我来说是逆耳之言,我非常挣扎。事实上,十五岁神呼召我去中国,十八岁离家去香港,这些事与神现在要我做的事相比,都要容易得多。
但主不停地将那个属灵的梅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:“你若想供养一个国家,就必须跳舞。”祂指的是那年开始的营会。我下定决心,营会期间每天都要跳舞。那时营会持续约一个月,现在持续十周半。第一天我很难为情,确信每个人都在看着我,都能看见我。其实在营会中,每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在灵里,几乎都不知道其他人做什么。当神的大能降临,恩膏降下时,你可能觉得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视你。但你很容易在人群中迷失,即使空无一人也是如此。大群天使和恩膏临在时,在你周围会发生许多事情。
第一天,除了在鞋子里扭动脚趾,我什么也没做,但我也明白了这个领域别人遇到的问题。在教导别人时,我常说:“只要把你的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,这就是开始。”不过我每天都准备好在主面前跳舞,一天天,我越来越放松。那个月底,主透过母亲向我发预言,她并不知道神正对我说的,甚至没人注意我试着跳舞。主对我说:“我要改变你的事工,我要差你到国王、王后、统治者、执政者中述说我的大能。”
我相信舞蹈能给列国带来的恩膏,我没有一天不跳舞,我甚至在在波音707、747和DC10飞机的洗手间跳舞——我是怎么做的?就是简单地直上直下。
每天你都需要恩膏在你里面流淌,跳舞带来恩膏。如果你在某地传道,没有跳舞的自由,就躲进衣橱里,在主面前跳一会儿舞。你若这样舞蹈,会带来恩膏将饼、肉、新酒供给列国。
发出先知性话语的同时,母亲在异象中看见“加德满都”一词。不久,主差我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(Katmandu, Nepal),和皇室成员谈论耶稣(此事和其它类似的事情都在另一本书提及)。主说,祂将差遣我们供给列国,祂会信守承诺,但要透过跳舞而来的恩膏实现,在舞蹈中赞美释放神的大能!
我们对一些中东地区的观念很陌生,但它们能帮助我们了解神。莎乐美(Salome)如何得到施洗约翰的头呢?王以她的舞蹈为美,预备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。她母亲欺哄她,让她要约翰的头,在这种情况下,跳舞起到了消极的作用。
在积极的意义上,我们跳舞、赞美取悦王,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赞美营造奇迹发生的氛围。
我跳舞时,总是能感到脚上的恩膏,也知道神的应许,凡脚掌所踏之地,都必归我们。
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,都必归你们,从旷野和利巴嫩,并伯拉大河,直到西海,都要作你们的境界。(申命记11:24)
恩膏临到时,我能身处美国,在灵里绕着耶路撒冷城墙跳舞。我跳舞经过大马士革门(Damascus Gate),然后继续深入到希律门(Herod’s Gate)那里,绕着圣司提反门(St. Stephen’s Gate),越过美门(the Gate Beautiful)结束,绕着粪厂门(the Dung Gate),越过锡安门(Zion Gate),上到雅法门(Jaffa Gate),再次越过新门(the New Gate),接着回到大马士革门。我能用受膏的脚绕着耶路撒冷城墙跳舞,始终为了耶路撒冷站立而相信神。用同样的方式,我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跳舞,我发现,如果你在属灵的领域里在列国上跳舞,神也会赐给你实际上在那里跳舞的机会。
我是英格兰西萨塞克斯郡奇切斯特(Nutbourne, Chichester, WestSussex, England)天主教圣经学校的赞助人。琼(Joan)和迈克尔·勒莫尔万(Michael LeMorvan)是创始人和董事。琼说:“路得,记得第一次听你说,你来我们这里事奉之前,曾很多次在英格兰地图上飞舞。我们认为这是所听说过的最夸张的说法。”
嗯,不论是否夸张,我做到了,我不是真的放下一张地图在上面跳舞,但我知道英格兰的形状。很多次我沿着北海(the North Sea)跳舞,从苏格兰到朴茨茅斯(Portsmouth),纵横交叉不列颠群岛(the British Isles),接着到爱尔兰和威尔士(Ireland and Wales)。出于主的负担和异象,我这样做。
这样真的有用吗?是的。你可以站在家乡,拥有列国,而舞蹈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。神将你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你,我们的脚受膏去拥有。许多教会有耶利哥行军,你绕着教会的过道跳舞,为教会、城市、各州、国家相信神而跳。是的,这就是灵里的耶利哥行军,虽然耶利哥城明显不在这儿。
有时,神在灵里把我提走,绕着白宫(the White House)跳舞,来来回回地从街道一侧到另一侧。你也可以做到:在灵里见到白宫,绕着它跳舞。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十六街(Pennsylvania Avenue and Sixteenth Street),经过购物中心返回,以这种方式,你将为你的国家收获祝福和得胜。
同样,我曾绕着白金汉宫、唐宁街10号和伦敦国会大厦(Buckingham Palace, #10 Downing Street and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)跳舞。在红场(Red Square),绕着克里姆林宫(the Kremlin)(为了俄罗斯复兴等事情)跳舞,绕着东西德(both Germanies)(为了德国统一)跳舞。我这样做时,想起亲爱的朋友,黛比.肯德里克(Debbie Kendrick)在德国统一前八、九年得到异象并发出同样预言,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已成为现实。我绕着州议会(the State Houses)和一个个国家的政府席位(Seats of Government)跳舞,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各大洲上跳舞。 在跳舞中彰显能力和对列国的恩膏。你越多在主面前跳舞,发现自己越有恩膏供给列国。天天跳舞,在舞蹈中赞美主,让这种恩膏从头顶直流到脚趾,在舞蹈中赞美主!
赞美是收割强有力的工具!

作者:路得.沃德.赫芙琳(Ruth Ward Heflin)
译者:路得(Ruth Ward Heflin)禧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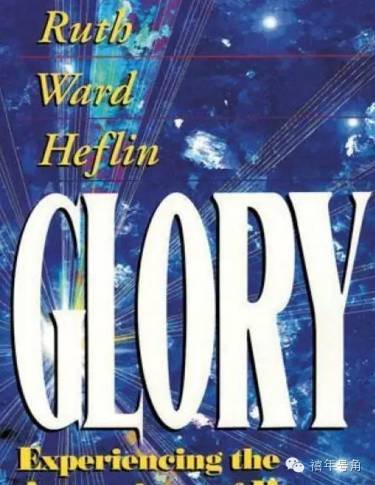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